试析谢林艺术哲学的体系及其双重架构
On the System and Dual Structure of Schelling’s Philosophy of Art
-
摘要: 谢林开创了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哲学,并首次在这个领域提出了系统的阐发。在谢林艺术哲学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及其与哲学(尤其是谢林自己的哲学)的关系中,包含着双重的架构,即永恒架构(艺术门类的排序)和时间性架构(即古代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对立)。谢林一方面洞察了艺术的永恒本质,另一方面也把握了艺术中的时代张力,从而为当代的艺术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Abstract: Schelling initiated the philosophy of art in the strict sense, and put forward the systematic elucid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is fiel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etaphysical basis of Schelling’s system of philosophy of art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hilosophy (especially Schelling’s own philosophy), pointing out that there are two structures in it, namely the eternal structure (the order of art categories) and the temporal structure (the opposition between ancient art and modern ar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bove point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how that on the one hand, Schelling has insight into the eternal essence of art, on the other hand, he has grasped the tension of the times in art, thus showing the correct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rt.
-
Key words:
- Schelling /
- philosophy of art /
- identity-philosophy /
- construction /
- end of art
-

 点击查看大图
点击查看大图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2389
- HTML全文浏览量: 4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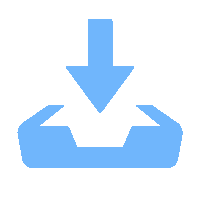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沪公网安备 31010102003103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102003103号